占星学:星相之学与历史故事
《后汉书•律历志》载有许多此类之事。王莽地皇三年,“有星孛于张南,行五日不见。孛星者,恶气所生,为乱兵。……张为周地,星孛于张东南行,即奨轸之分。翼轸为楚,是周楚地将有兵乱。后一年正月,光武起兵舂陵。”孛星即彗星,俗称扫帚星,占星者视为兵乱之兆,孛星潜入翼宿、轸宿,是其对应区域楚国将有兵乱之兆,“后一年正月,光武起兵舂陵(按:舂陵,古县名,治所在今湖北枣阳南,屑古楚地),即是其验;汉安帝永初四年六月,“太白入舆鬼,指上阶,为三公,后太尉张禹、司空张敏皆免官。太白入舆鬼为将凶,后中郎将任尚坐赃千万,槛车征弃市”。占星者以为太白(金星)入舆鬼(鬼宿)不利于三公和武将,张禹、张敏免官,任尚被杀,都是其凶兆之应。星象与人间灾异祥瑞的联系越來越被人们看重,天人感应被史家当正史、用史家的语言记录了下来,就连以人物传记为主的《三国志》亦深受影响,它虽无专志记载,却在人物纪传中叙述星象之事,《魏书•武帝纪》就有“桓帝时黄星见于楚、宋之分,辽东殷馗善天文,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、沛之间,其锋不可当”的记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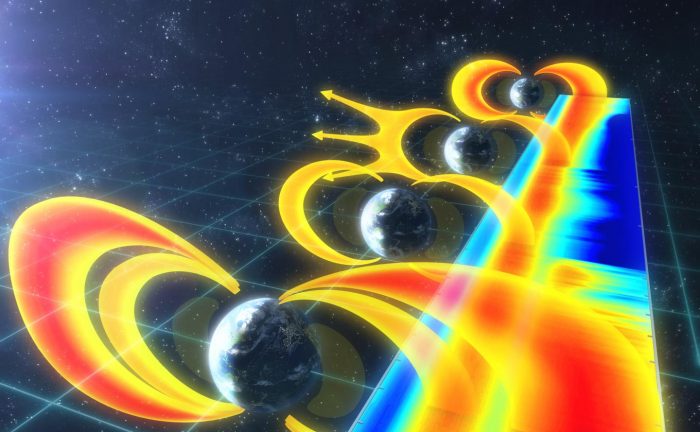
与中国古代其它术数比较起来,占星术有其独特之处。说它独特,不仅仅是因为它通过观察星象的变化来占验人间吉凶灾异,而且主要的还在于它极少涉及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,平民百姓甚至下层官吏有疑惑厄难,如要求问吉凶,他们向拆字算卦的术士求教,也决不去求助星士。许多人看来,占星术是与他们无缘的星相学古籍,因为他们自知不是“上应星象”的人。占星术的对象是玄奥莫测的星空自然变化,而其目的则是占验那些“上应星象的人或事的吉凶灾祥。哪些人和事“上应星象”呢?从正史、笔记、小说及其它文献记载来看,大致包括天灾兵乱、朝代更迭等国家大亊和帝王将相、公卿大臣的福祸休咎两大类。
据《晋书》记载,西晋时,有个叫戴洋的人精于占星望气之术,扬州刺史陈徽曾向戴洋求问吉凶,洋答道:“荧惑入南斗,八月暴水,有客军西南来”。至八月,果然出现了水灾,张昌部将石冰率军自荆州来犯扬州,击败陈徽,占领扬州诸郡。当石冰势力方炽之时,戴洋又对人说:“视其云气,四月当破”。次年(晋惠帝永兴元年,即公元304年),石冰果遇害,张昌起义失败。东晋明帝太宁二年(324)正月,有流星东南行。洋曰:“至秋应当寿阳。”及王敦反叛,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向戴洋求问其胜败,洋答道:“太白在东方,辰星不出。兵法:先起者为主,应者为客。辰星若出,太白为主,辰星为客。辰星不出,太白为客,先起者败。今有客无主,有前无后,宜传檄所部,应诏伐之。”辰星即水星。《史记•天官书》“辰星不出,太白为客。其出,太白为主。”戴洋正是按照司马迁的主客理论来解释太白金星的出现的。祖约竟然相信星家之言,起兵讨王敦。不久,王敦病死,祖约勒兵寿阳,应当初“至秋应当寿阳”之语。此时,戴洋又对祖约道,“江淮之间,当有军事。谯城虚旷,宜还固守。不言然者,雍丘、沛皆非官有也。”祖约不从,结杲豫土尽失。
戴洋见荧惑入南斗知有水灾和兵乱,见太白出东方,辰星不出而知王敦当败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诸葛亮却能观天文而知月内大雨琳漓。曹真引四十万大军宼蜀,诸葛亮听到这个消息,令张嶷、王平各引一千兵士去坚守陈仓古道,阻挡魏兵。二人道:“人报魏军四十万,诈称八十万,声势甚大,如何只与一千兵去守溢口?倘魏兵大至,何以拒之?”诸葛亮道:“吾欲多与,恐士卒辛苦耳。”张嶷、王平都是能征惯战之将,闻此语不由得面面相觑。他们知道,以二千对四十万,无疑以卵击石,是白白送命,故而皆不敢去。不料诸葛亮却没事一样,只管催二人去:“若有疏失非汝等之罪。不必多言,可疾去。”二人仍不敢去,又哀告道:“丞相欲杀某二人,就此请杀,只不敢去。”诸葛亮见二人如此害怕,笑着说:“何其愚也!吾令汝等去,自有主见。吾昨夜仰观天文,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,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。魏兵虽有四十万,安敢深入山险之地?因此不用多军,决不受害。吾将大军皆在汉中,安居一月,待魏兵退,那时以大兵掩之。以逸待劳,吾十万之众可胜魏兵四十万也。”二人听罢大喜,领命而去。曹真率大军至陈仓城,见无大军防守,令继续进兵。副都督司马懿谏道:“不可轻进。我夜观天文,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,此月内必有大雨。若深入重地,常胜则可,倘有疏虐星相学古籍,人马查苦,要退则难。且宜在城中搭起窝铺驻扎,以防阴雨。”果然,未及半月,天降大雨,淅淅漓漓了一个月,陈仓城外,平地水深三尺,军器尽湿,人不能睡,昼夜不安,马无草料,死者无数,军士怨声不绝。曹真和司马懿只好撤军。诸葛亮观天文知有连绵大雨,以逸待劳,不战而胜。
星士、星家把玩的占星术,玄奥诡谲,神秘莫测。不幸的是,史家相信它,小说家相信它,那些些严肃的考据家也相信它。明郎瑛《七修类稿•天地类》“天狗星”条载:
元至正六年,司天台奏称:天狗星坠地,始于楚,终于吴,遍及齐、赵诸地,但不及于两广。当血食人间五千日也。时云南玉案山忽生小赤犬无数,群吠于野。占者曰*“此天拇坠地,有大军稷境”。又,父老传,太袓登极后,每日市曹杀人之处,夜有一大白犬食血。予意徐寿辉、韩山童、陈友谅、明玉珍、倪文俊辈,俱起湖湘,而南直、吴中尤盛焉。其后山、陕、滇、蜀四方俱有甲兵之祸,唯福建、南广,王师到即出降。以是占之,则占验人传之说,讵不信夫!
天狗星,古以皆以其为凶星。《史记•天官书》载:“夭狗,状如大奔星,有声,其下止地,类狗。”郎瑛以后来出现之事,附会元至正六年司天台之奏,以元末诸农民起义军俱起湖湘附会天狗星坠地“始于楚”,以“南直、吴中尤盛”附会“但不及于两广”。这样附会的结果,自然是对星士之语深信不疑。郎瑛不仅相信天狗星坠地将有兵乱之说,而且对其它星象变化引起的天人感应现象也颇为相信。同书“星验”条记载了三件事,一是“中台星常坼”,二是“北斗七星第四星常不明”,三是“彗星扫文昌”。星有三台,分上台、中台、下台,共六星,两两相邻,起于文昌星,列抵太微垣>古代常以星宿象征人事,故称三公为三台,《晋书•天文志》称:“在人曰三公,在天曰三台。”中台星常坼,是说中台星常常分离开,不能两相比邻。何以会出现这种星象变化呢?郎瑛引用别人的话说:“或以上下不交,或以本朝不立宰相之故”。他不是从星象自身的变化去寻找,而是认为天人没能相应。他又引东汉张衡“中台主宗室”之说,认为中台星常坼,象征着宗室分裂,并举明武宗正德后安化宁王二藩叛逆,楚世子枭首二事证之。北斗七星中的第四星即天权星,星家以为是主时令之星,天权星常不明,以至地上四时失序,桃李冬华,雨阳不能以时。郎瑛还据张衡天权星“不明或变,朝廷废正乐”,怀疑“今之乐果古之元声乎?”言外之意是,今之乐既非古之充声,当非正乐,而正乐废,上则有天权星不明应之。郎瑛征引古今,为中台星、天权星的变化寻找理论的和现实的根据。彗星为凶星,“彗星扫文昌”,意味着文昌星对应的人事将有噩运。文昌星是斗魁上六星的总称,《史记•天官书》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”。星家以为文昌星是主文运的星宿,彗星扫文昌,则文运衰微。郎瑛接受了这种迷信观念,认为宦官刘瑾设内行厂,内阁被逐,九卿被祸,正是文运之厄,郎瑛由星象变化推及人事,由人事反证星象变化,正是为了证明“星验”。
